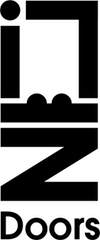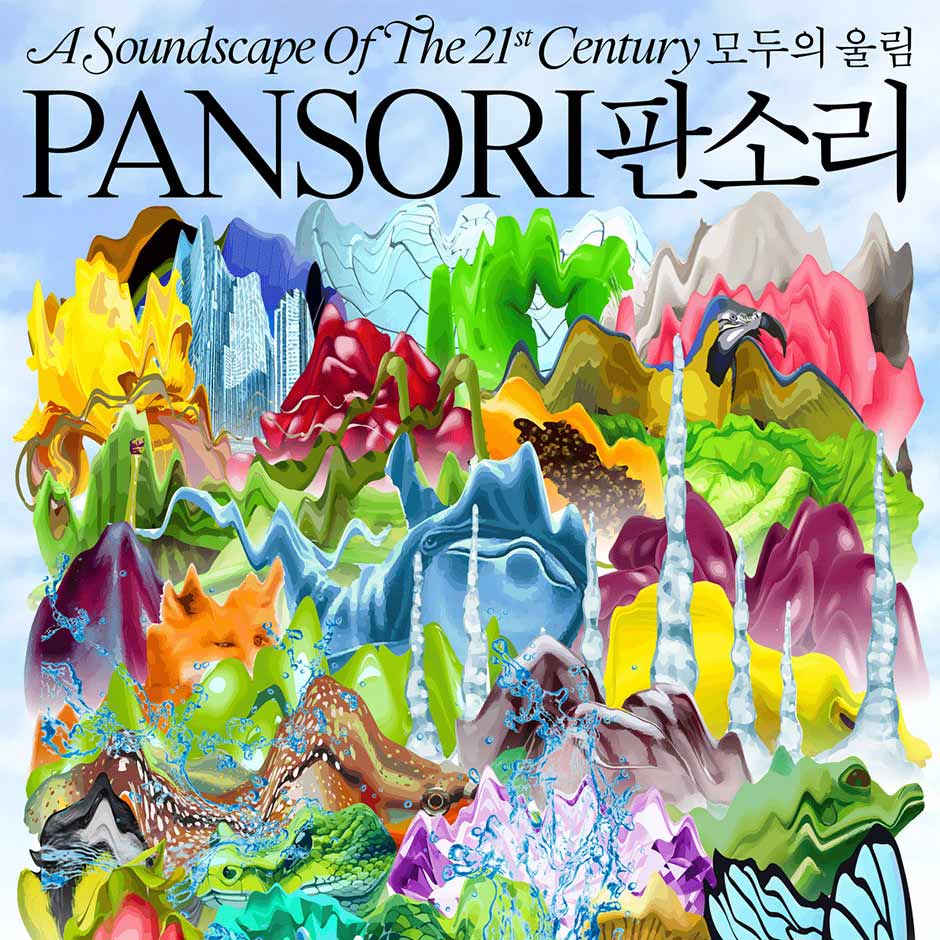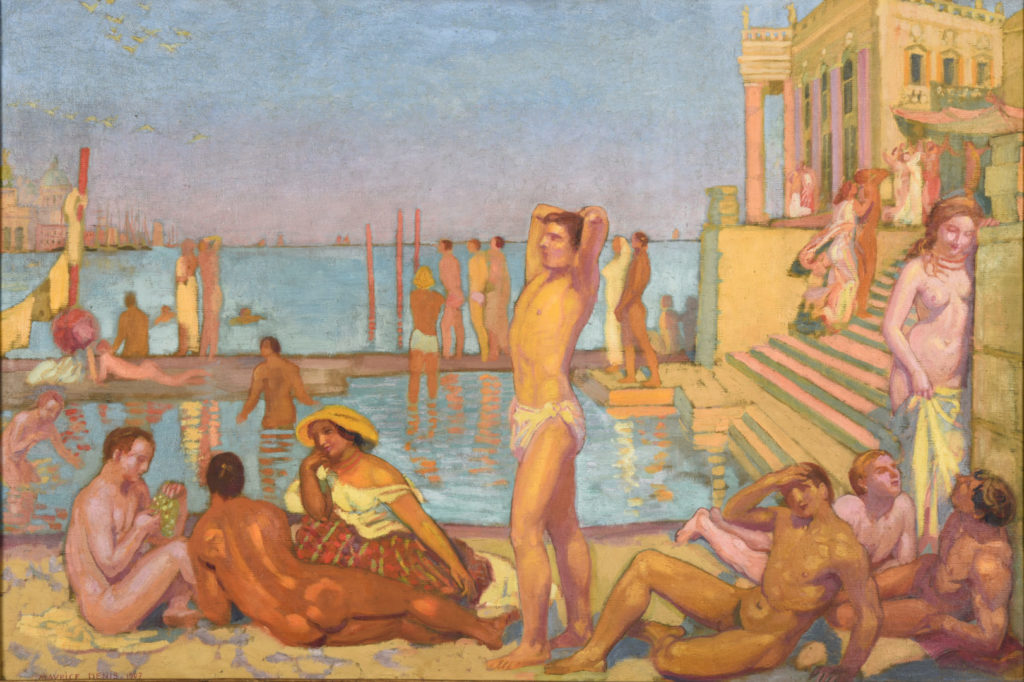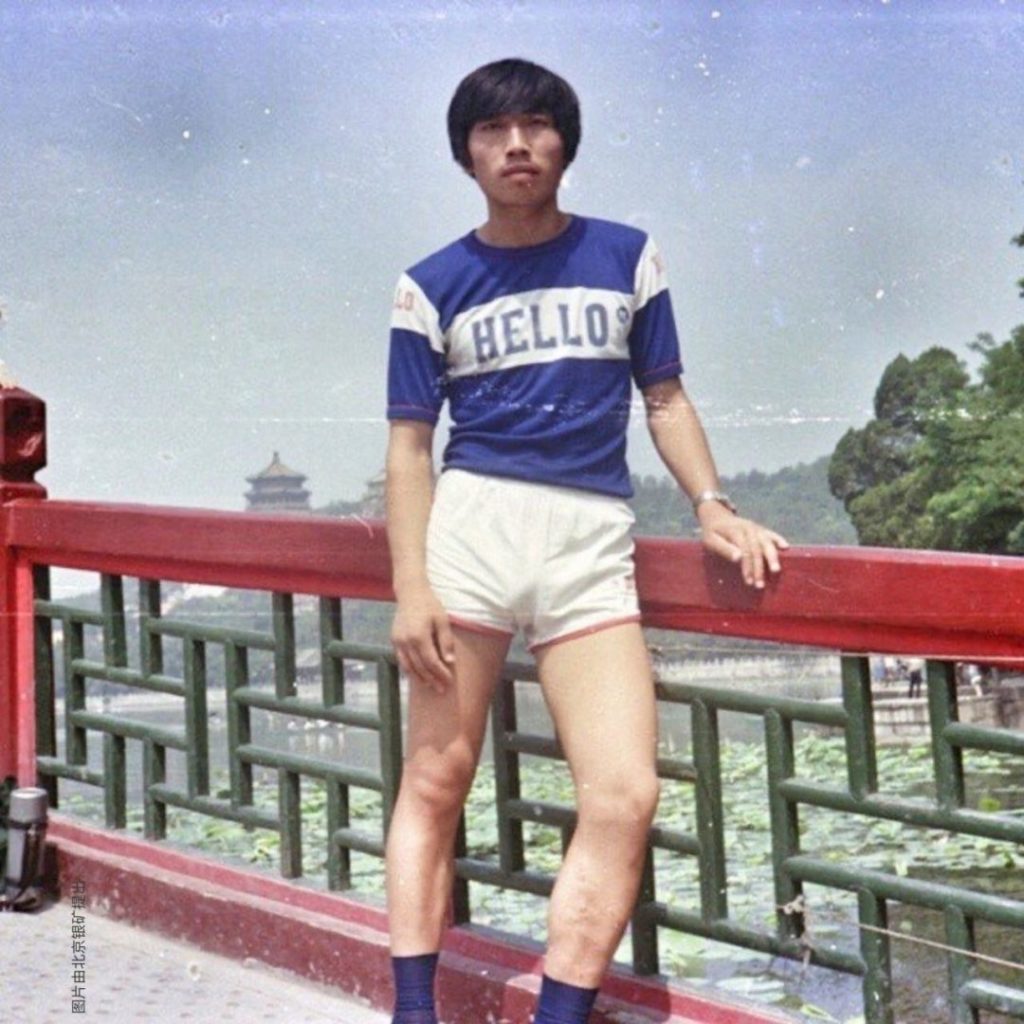尼古拉斯·伯瑞奥德,策展人、作家、艺术评论家和理论家,提出了“关系美学”概念。2000至2006年,他与热罗姆·桑斯共同创办了巴黎东京宫,并担任联合总监。他也曾担任过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的当代艺术策展人、基辅维克多·平丘克基金会的常见顾问、法国文化部艺术创作监察局局长,以及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院长。他还曾是蒙皮利埃当代艺术中心的创始人及总监。2022年,他创立了策展合作社Radicants。
本专访载自LEAP杂志中法特刊《不居》的“艺术与生态”系列对话(2024)。这本新刊旨在从跨学科的中法视角出发,激发艺术家、评论家和研究者对当代艺术和跨文化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讨论。
采访:Victoria Jonathan(零零)
翻译:林雨松、黄黎娜